读夏坚勇《承天门之灾》:一和它后面的那些零 | 南通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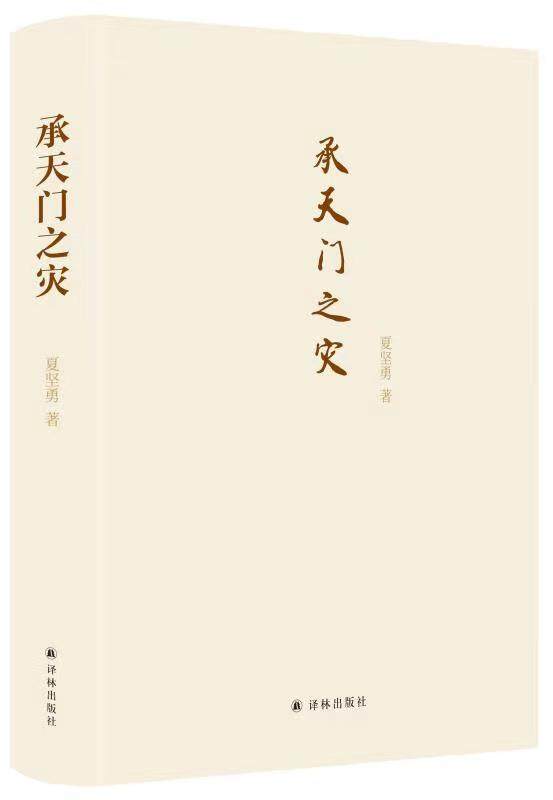
我决心写几句话,说说夏坚勇的《承天门之灾》,把有些想法封印在小文章里。这样我就得救了。因为自从看了这作品,时不时就会想起它,脑海里现一下。干扰我写别的东西。不说点什么,不得安生。这就是为什么《钟山》已经发了好几个月,我才开始说它的原因。
不客气地说,散文在小说面前,真有点灰头土脸的。夏坚勇凭一己之力,撑起了散文的脸面。谁敢说《承天门之灾》不如一部小说呢。完全可以拿它当小说。但是人家却说自己是散文。我想这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因为骄傲。每一个细节都有根据。雕花刻镂一样的。花了足够多的笨功夫。一呼一吸都是宋朝。
写这种东西,是要呕心沥血的。先吃草,再吐奶。绝大部分的力气要花在前期功夫上。而真正动手写的功夫,也不比一部小说少。所以说写这样一种有根据的东西简直花了同等长度小说的几倍功夫,完全有理由傲视。我拿它当历史小说。
每每读有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心里会不自觉告诉自己,这是小说。因为就是一个小说的样子。明明白白地知道,虚构。我知道他在虚构。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在虚构。他还是在虚构。我也接受了这种虚构。而阅读《承天门之灾》,我的潜意识里又明明白白知道,这是历史小说,也不只是历史小说。处处皆细节,江水奔流,庞大充沛。《承天门之灾》的细节兵团打败了我的潜意识。确凿无疑地,我承认了,那些事的确是真的,非虚构。虽然也未必就全是真的。是上了作者的当。
气足。这是我们读夏坚勇的共同认识。不止我。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也都十分地承认。所有的历史题材作家里头,夏坚勇是气足的。气足便夯实了文本细节。你的前期积淀大于文本细节,就会显得气息稳定绵长。我不敢想象夏坚勇在宋史上所花的功夫。在我看来,可能他根本就生活在宋朝。所以沉积了那么多的细节功夫,一整块的木头。扛起鼎就走。或者,透雕。要是气不够,就会大刀也舞不开,气喘吁吁,断断续续,内力不足,浮的,更不要说扛鼎了。或者,拼接,打木工胶,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大块好木头给你透雕的。
没有什么积淀又不想气虚怎么办呢。让叙述小下来。怪不能都会对有些张口家国情怀闭口人生苦难的文章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没有活气,全是僵词,当然令人反感了。有些坏文章读完让人头上顶铁。真坏。
以上说的全是夏坚勇笨的地方。一后面的那些零。没有零,“一”也就只是一。有了零,“一”才有可能无穷大。所以说,好东西是聪明人花笨功夫写出来的。这是夏坚勇自己说的。笨功夫是必定要花的。花完了笨功夫,也不一定就写出来好东西。也要聪明,有巧劲。会挪腾。这就是那个“一”。有了这个“一”,《承天门之灾》读起来便像小说。有小说的味道。有了这个“一”,那无数个零才有了活气,会行走,有生命。
当然,夏坚勇深谙此道。他从来都不缺少这个“一”。整部作品里类似“兵荒马乱是因为大街上确实有‘兵’和‘马’,他们是到城东的汴河码头仓库去背粮的。”这样的活气之句,比比皆是。
又比如:“年号就像个旧式女人,夫君得意之时,她就是诰命夫人,光鲜且体面。夫君一旦流年不利,就要弃旧迎新,这时年号就成了冲喜的侍妾。”狡黠的叙事人时不时就跳出来,全权在握。在你的上方,全知全能,进行指引。这便是夏坚勇的狡猾之处。作为叙事者,他决不甘心被历史覆盖。他要跳出来,指点江山。这是时间赋予后来者的权力。他决不放弃。
也许有些人不缺这个“一”。但是缺那后头的那些零。那种深厚的背景,那种吹尽黄沙始到金的细作功夫,那种排兵布阵的耐心和力量。你可以想象,纨绔子弟夏坚勇坐进了无数个夜深人静,把玩这段历史,把玩手把件。把历史盘出了包浆。于是历史便面粉一般,手指上流过。泥人张塑造了它。大白天捧出来。
这样的功夫最是伤人的。简直是在吐血。比如我,就只有耐心写一点零头碎脑的读后感。享受美食,吃就对了。至于做大厨,嘿嘿,那还是留给雄心壮志的人吧。写作难道不是一种最妨碍正常生活的行当吗?把自己全都泼出去。你要舍得。从《绍兴十二年》,到《庆历四年秋》,再到《承天门之灾》,夏坚勇的宋史三部曲吸引我追下去的魅力,很大的原因也在于他的“懂人性”。帝王君臣,都是人。懂人性自然也会懂帝王。不过是将心比心,贴近各人心理罢了。所以说,宋史三部曲,精彩的其实是把握了幽微的人性。那种历史事件前,各色人等的权衡,真是精彩。
《承天门之灾》里头有一个坏女人,特别使我佩服。我以为她是非常有政治智慧的。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竟能生存得很好。最令我佩服的一件事是她处理“官家”留下来的政治遗产,简直不动声色。她就是刘娥。书里对这件事一带而过。我只是举个例子。
说到最后,必须要说一下《承天门之灾》的主体事件,其实就是“降天书”。不自信的皇帝赵恒一直制造天书事件来为自己的正统背书。当然是不可能降天书的了,除非是在梦里。于是围绕“降天书”事件,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乃至最后一场大火。“北宋遂亡”。赵宋王朝在历史的火焰中灰飞烟灭。
归根结底,承天门之灾,是谎言之灾。作为读者的我们,是深可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