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缘 | 南通发布
读书看报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习惯,喜欢看报这是我在上高中时,一位同学帮我培养的习惯,为什么是我的同学帮我培养的习惯呢?因为这位同学是我们校刊《蛙潮》文学社的社长兼主编。他经常给省、市报社及县广播电台写新闻、通讯及纪实文学。在众多的男同学中,我跟他走得比较近。他温文尔雅,待人接物总是彬彬有礼。有时星期天我还骑自行车去他家蹭饭。由于我俩关系好,他就拉我“入了伙”,负责报纸的校对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没有工资的工作。
校刊的组稿、审稿、编辑都是我们社长负责。有时候为赶一篇稿要忙到下半夜,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那时的校刊大多是刻钢板油印,后来慢慢改成活铅字排版打在蜡纸上油印。首先要选好稿子,然后进行排版,排版后交给刻钢板的人去刻字。如果有插图,先把插图选好位置先画上,然后再在规定图框里刻上字。我做的是校对工作,正常是文稿确定好以后,就交给我看一遍,排版后我再校对一遍,刻好钢板后,我拿着原稿对照蜡纸上刻的字,再一遍又一遍,每一个字过一遍,发现错别字直接画圈或者把错的字涂掉。发现漏了的字,在字与字之间画个Ⅴ字符号,然后再在V字中间刻上所漏掉的字。修改得多了,有时候报纸出来,有一大把小圈圈。校对好了下一步就是油印,油印机是木头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木斗盒子,只是没有盖,盖是油印网框,一头用两副小铰链连着另一端盒子框,油印正常都是社长亲自操作,把刻好的蜡纸,贴在油印网背面,印油框里倒上印油,用滚筒来回地一滚,一张张油墨香的报纸就这样出来了。记得第一张报纸出来了,我们俩很兴奋,拿着报纸笑得合不拢嘴。报纸每个班都有十几份,但我们班特殊照顾点,基本上都能达到两个人一份。当时,报社经费正常都是校团委的经费,不够的社长自己贴一点。我的新闻稿和通讯就是跟他学的,他教我如何开头,例如:本报讯等。其实写新闻很简单,怎么发生的就怎么写,最后不要忘记“落款”也就是谁报道的就行了。那时写新闻稿件要找单位盖章,以确认其新闻的真实性,我们在学校写的新闻稿件大多数是他去盖章,他跟学校领导比较熟。1988年的植树节我们就写了一篇新闻稿,还被新华日报采用了。虽然只有豆腐块大的新闻,稿费只有十块钱,为此我们专门到校门口烧腊肉店打牙祭,点了半斤猪头肉和一人一瓶汽水,庆祝一番!从此,我便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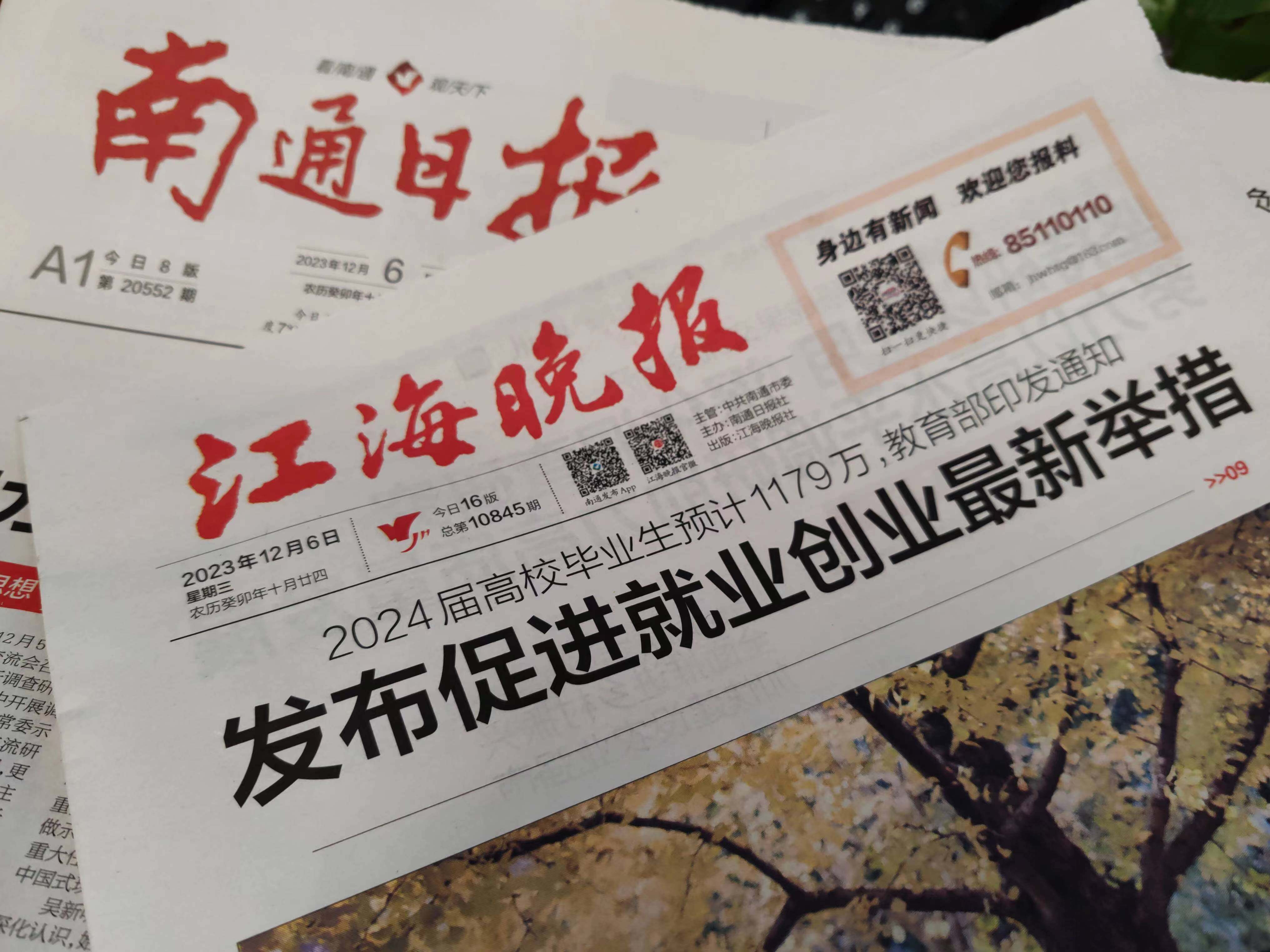
前些年,我还喜欢每年订一份报纸,《江海晚报》《扬子晚报》《文摘报》《现代快报》等等,近几年,由于网络普及等原因,不怎么订报纸了。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看报纸都要推开眼镜,贴着鼻子看。要么戴着眼镜手推得老远看,否则看不清楚。即使捧着手机看,看一会头就感觉头发晕,眼发花。正如作家陈年喜写给儿子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没有那种手捧报纸的进入感、那种交融、碰撞、思维在纸上的流淌铺展感”。我们这一代人还是习惯于读纸质文字。
不再说了,今年提前订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