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读王维最好的时代丨专访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王志清教授 | 南通发布
今日重阳。一千多年前,十七岁的王维独居偌大的长安,凭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七绝,年未弱冠,名动天下。
“此诗绝妙!字法、句法、章法无有不妙”,王维研究专家王志清教授对这首千古名篇推崇备至。刚为光明日报社报业集团杂志《博览群书》编纂“重阳文咏”的王教授在栏目编者按里说:古人擅诗,重阳节里必诗酒酬唱。重阳文咏,也成了一种很重要的诗词题材,进而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情感文化符号,因此重阳节也留下很多一流好诗。而其中最为脍炙人口者,莫过于王维此诗。1980年,该诗还被法国巴黎市民公投为唐诗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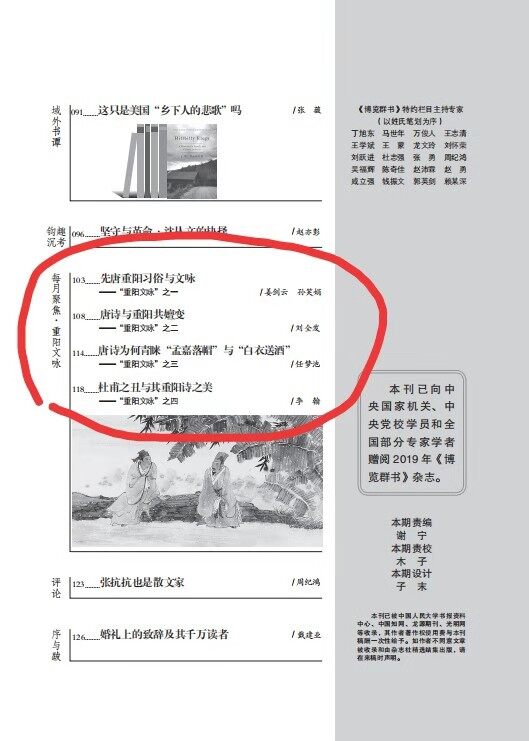
《博览群书》“重阳文咏”栏目录截图
研究王维已逾廿载的王志清教授,在《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提出一个全新的学术预判——“盛世读王维”。
本周,这位被学界一代宗师霍松林先生评为“探微抉奥、新意迭出、有开疆拓土之意”的王维专家接受南通发布记者专访。

王志清教授资料图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记者:王教授您好!史载王维九岁知诗词、工草隶、晓丹青、通音律;十五岁独自离乡进京,诸王豪右“虚左以迎”;二十出头进士登第。《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即成于他少年得志这段时期。现在看来,此诗浅近素朴近乎口语,您却认为此诗绝妙,妙在何处?
王志清:此诗领起之“独”字,可谓诗眼,统摄全局,诗情全由“独”字引发,也皆在“独”上落实。前两句直接破题,不经迂回迅速高潮。但这种写法往往让三四句难以为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若按一般思路顺势思念怀人,则会流于平直而后劲不足,“续”以狗尾。
王维的高明之处,正在其三四句上,来了个“遥想”手法。这个“遥想”其妙有三:其一妙,是在于诗人不直说自己忆念,而以“遥想”呈现所忆念者,诗意萦纡;其二妙,是诗中不写自身的异客处境,而以“登高”与“插茱萸”来写对方的欢会情景,更显示出身不能至的加倍缺憾;第三妙者,用“遥想”来设想对方,好像遗憾的不是自己,反倒是兄弟。这种写法可谓:写身在此地而想彼地之思此地,写时在今日而想他日之忆今日。
王维最喜欢用“遥想法”,以我推人,明明是我想别人,却反说别人想我,由此忆念之情更为深切,加倍凄凉。后来杜甫的“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是这种写法,白居易的“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也是这种写法。
记者:我们想学习运用这种手法的话,该如何操作?可否“请”王右丞再示范一二?
王志清:再举一首唐诗中第一等的名篇——《送元二使安西》。这也是一首妇孺皆知的七绝:“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单从字面上看,实在平平。前两句写送别时的节物风光,平平;后二句表达送别之意,也平平。但这首诗何以成为明清两位大家——胡应麟与王士桢口中的“唐诗压卷之作”?我认为在于两大妙处,一是恰到好处的“截取”,二是更为精进的“遥想”。
恰到好处的“截取”怎么讲?绝句的“绝”源于晋宋诗人“四句一绝”的概念,此前诗经、乐府也多以四句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这是中国古诗的习惯。正因绝句形式短,便更讲究“截取”,故而绝句的艺术,某种意义上就是“截取”的艺术。我们现在看这首《送元二使安西》,王维仅截取了“劝酒”这一个镜头,一刹那间,十分浓郁的感情浓缩于一瞬精粹。
更妙的是这里的“遥想”。友人出使哪里?安西!安西是何处?即安西都护府,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而特设的都护府,自古便是汉家政权的军事要塞。王维所处的时代,西面吐蕃、北方突厥不断侵扰唐境,此时友人出使安西意味着什么,送者与被送者都心知肚明。
古来征战几人回。此时说什么,不说什么,怎么说,既关系到送别是否得体,也是送别诗高下优劣的关键所在。
王维说的妙极了!“西出阳关无故人”。他不说以前的友情怎样如胶似漆,也不说眼前是如何难舍难分,而是说日后——遥想“西出阳关后”,你我可就再也见不到彼此啦!
这时回头再看第三句的“劝酒”,看那千言万语凝成的一句话:再喝一杯这离别的酒吧!我们就会感到其中无限离情别意溢于言表。
王维此诗的高明之处,即“截取”极具镜头感的临别一瞬,再以“遥想”展开,字里行间流出震烁千古之情感,更应了那句清代大家张谦宜那句——凡情真以不说破为佳!
他的“遥想”诗还有不少,多见于送别诗,比如《送平淡然判官》《送韦评事》《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军司马》《送贺遂员外外甥》等,大家可以多加品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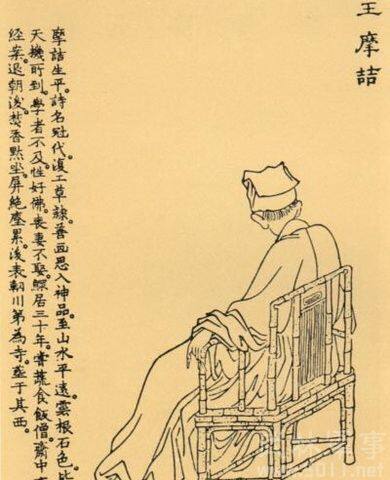
王右丞画像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记者:听您所说,王维写诗似乎挺爱“绕着写”,或者说是“虚写”。其诗今存四百余首,除了“遥想法”,还有什么运笔风格?
王志清:确实是这样的!从王维今存的比较可信的约四百首诗来看,他极喜虚写,也极擅虚写。但他的虚写不是“拐弯抹角不说人话”,而是含蓄蕴藉不直接说,通过创造“意境”来暗示读者。意境,是中国诗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最能体现中国美学的特色与贡献,王维则将意境做到极致。
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山居秋暝》。世称王维“五言宗匠”,这首五律可谓王右丞五言典范。在我看来,这首诗妙不可言,可谓诗中之诗。其诗开篇劈头就是一个“空山”,其妙无比!妙在何处?暂且不表,等读完全诗回过头来看。
诗的中间二联二十字,笔法错综,极尽变化之能事。先看颌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侧重写景,上句月光抚松,由远而近,下句泉流石上,由近而远;再看颈联“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侧重写人,上句浣归喧笑,由隐而显,下句莲动渔舟,由显而隐。这二十个字,高下远近、动静显隐,无所不包。行诗至此,美不胜美,景象写到极致后,以“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来收束,他不说好与不好,而是反用典故,诗旨出矣!《楚辞•招隐士》里说“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但王维却说“可留”,这既是“色空不二”之禅理,也是儒家“无可无不可”思想,更是一种“天如何人亦如何”的天人合一哲学,表现了一种的居所,表现盛世无处不桃源、无处不适合人诗意栖居的诗意理念。
我们现在再回头看诗开头“空山”二字,简直要让你拍案叫绝了。何谓“空山”?“空山”不空,“空山”美极万有,王维营造的这种“空山”,让我们从中感受和体悟到一种比实景更为高级、充满空灵神韵的“意境”美。
现在你发现了没?这首四十字五律,其实只说了一个字——“空”,所有意思都在为这第一个“空”字作注脚!纵览全诗,你会悟出这里的“空”,不是视觉上的“空”,而是脱去胸中尘浊后对现实人事的认知,空的是心,不空的是境。王维太喜欢用“空”字了,三百多首诗中多达八九十次,其实这是在造境,所造皆空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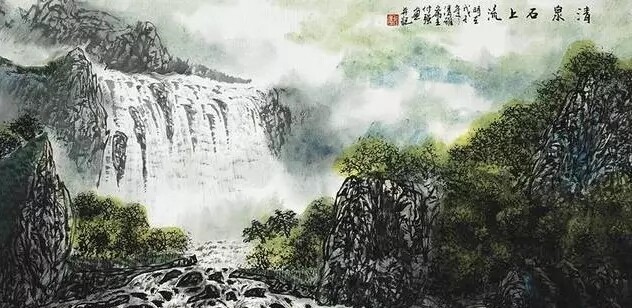
记者:我们一般接受的教育是行文须“言之有物”,但看王维诗多为“言之无物”或“意在言外”,这是否背离了课堂美学?或者说鉴赏王维诗作该用何种美学眼光和思维?
王志清:其实《山居秋暝》还不算太虚,毕竟尚有二十字实景。王维还有更“狠”的,譬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其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句,最常为人引用。
此诗可谓全盘“虚写”,王维旨在表现他隐居山间悠闲自得的心情,可竟无一句描写具体山川景物,偏又诗意饱满,理趣横生。这就涉及到我所常提起的一个观点:王维实现了中国诗歌由质实而空灵的美丽转身,强化了中国诗歌的形而上学性,也使中国诗学开始以“境”为上,以“逸”为上。
我在《王维诗选》前言中说:王维的诗,是诗的哲学,是哲学的诗。王维与李杜,他们的诗,都有哲学支撑。他们各自又都有哲学的倾向侧重。众所周知,王维耽禅,其名维字摩诘亦为其母取自“维摩诘”之名。然而,儒释道在古代又是不分家的,仅仅是侧重而已。《终南别业》中的生态智慧,恰是将老庄之“无我”、禅宗之“空虚”与儒家之“和乐” 三位一体的最佳体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兴至神会,只有过程,没有结果,也不问结果。禅宗“空诸所有”的要义,移植到审美和生态上说就是“物我两适”。
古人评价该诗为“天怀淡逸,超然物外”“如行云之在太虚,流水之无滞相”。我们今人更应看到诗中体现出的生态观与生态智慧,即自然中心主义,以生态为中心,以自然为中心,而非以人类为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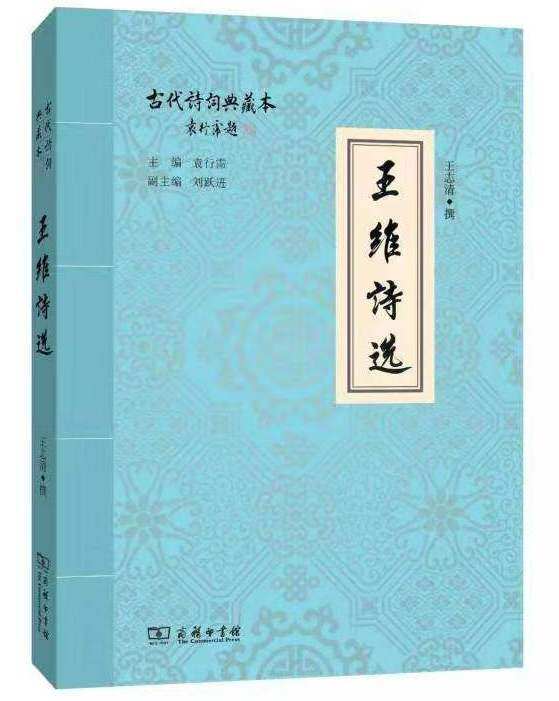
王志清所撰《王维诗选》封面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记者:我们翻阅您多部著作,发现您一直坚持认为王维诗作才是“盛唐正音”。这与我们一般理解似有偏差,盛唐难道不应是河清海晏、物阜民丰、万国来朝、豪迈尚武的磅礴气象吗?王维这些偏“佛系”的诗文,如何能代表充满生命力的盛唐正音?
王志清:要说清“盛唐正音”,很棘手。这里不妨浅说一二。
何为“正音”?正音反映的应是时代主流和社会本质。既是“盛唐正音”,就该是盛唐社会风貌与时代本质的客观反映,是盛唐精神和盛唐艺术的主旋律。
那何为“盛唐”?唐昭宗时著名的宰相诗人郑綮在《开元传信记》中说:“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 郑綮生活的年代虽距“开元天宝”已去百余年,但比《旧唐书》成书时间早了六七十年,其记载应基本属实。
这样看“盛唐”,你会发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国力极盛,二是全面和谐。特别是和谐,这是盛唐最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盛世的突出特点。当代学者李从军在《唐代文学演变史》中说盛唐的这种和谐,“是要多少时代的漫长时间才适逢其时”。
古人云“听音知治”。所以,“盛唐正音”首先必须是和谐之音,不是杀伐之音,至少不是愁苦之音。
而王维诗,正是盛唐盛世产物。他的一生,几与盛唐同步,他的价值观和审美思想,是盛世的。你看王维诗,最突出的特点是“静”,他不出直言,更没有妄言狂言。他安静地反映着光风霁月的盛世气象,温和地描写着人在盛世自有诗意的生存状态。
比如《新晴野望》“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放眼原野,一尘不染,更别说有什么乌烟浊垢了;比如《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日本学者川合康三从中读出无边际的世界整体,与其说实景,不如说是盛唐人共有的安定世界观。这些是什么?这些是盛世才有的“自信和潇洒”!
但王维也不是完全这般秀逸典雅,他也有豪迈意气、瑞丽飞扬的句子,而且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惊绝!
要在唐诗中遴选两句最能精妙反映“盛唐气象”的句子,恐怕没有比“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更合适的了。这是王维的一首七律和诗,全名《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和的是为唐玄宗作传位册文的中书舍人贾至所写《早朝大明宫》一诗。
这两句诗,气象高华,仪态万千。九天阊阖开宫殿——早朝开始,巍峨宫门层层叠叠,如九重天门迤逦打开;万国衣冠拜冕旒——八方官员、万国使节跪倒丹墀拜谒天子。这是何等雍容、何等璀璨的盛唐气象啊!《唐诗观澜集》评价此诗“日月五星,光华灿烂”,诚哉斯言!
记者:接下来这个问题或将带来争议了。既然您说王维是“盛唐正音”,那么李杜呢?毕竟韩愈一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已为后世定下大唐三百年“李杜分霸”的诗学基调。
王志清:要说清“盛唐正音”,王维与李杜真少不了一比。但请注意,虽作比较,却不是比孰优孰劣。
三人都有不少写山的诗,我们就以此来比!
先说杜甫。老杜有三首《望岳》,分别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各作于开元、乾元、大历三个时期,恰好代表他青年、中年、老年三个阶段。
其中第一首我们非常熟悉:“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该诗气骨峥嵘,体势雄浑。“决眦”二字尤为传神,俯瞰一切,傲视天下。注意了,这正是杜甫区别于王维的关键所在!用前面提到的“有我”与“无我”二境来说,杜甫是“有我”,全诗主旨就是“总有一天我要傲视天下的”。联想到当时他洛阳应试落第的背景,老杜似乎在怄气,又似乎在赌气,反正是气不顺。用金圣叹的话说是“想见其胸中咄咄”;用叶嘉莹授业师顾随先生的话说是“比较直”;用川合康三的话说则是“通篇显出人和世界的紧张关系”。这哪是盛唐该有的积极气象?!
再看二三两首,则是“气骨顿衰”了。写华山是“稍待秋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这是“问天”;写衡山则是“祭天”——“三叹问府主,曷以赞我皇”,我到底有什么不是呀?这二首情绪非常低落,是悲声哀音,更不是“盛唐气象”了。
接着说李白。他在入长安前后,写了不少与山有关的诗。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登太白峰》: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
我们认为,该诗写于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写的是一种失望、失意而生成的惆怅、苦闷。“何时复更还”,想想李白当时的境遇,被逐出京城,又恋阙难舍,欲去而难行,实在耐人寻味。
再看李白写山诗作中最长的组诗《游泰山六首》,五言九十六句,篇篇写神仙与仙境。我们来看“六首其三”,真可谓凄凄惨惨戚戚: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意,其实是他以“仙”来自我麻痹,远离现实解脱失意;然而,笑我学仙晚,蹉跎凋朱颜——如今一大把年纪了,仙途与仕途两空,莫名懊恼;最后,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太伤感了!
李白写山名气最大的应是那首《蜀道难》,可谓奇之又奇。可你猜与贾岛齐名的姚合怎么说?姚氏在他编的《极玄集》中说:“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啥意思?你看李白当时的际遇——该诗写于开元十八年,正是他第一次赴长安求仕失败,无成之羞愤之际——他是在借蜀道之畏途以喻仕途之坎坷、喻失志之幽愤。用现在的话说,李青莲其实是在“吐槽”啊,分明就是盛唐声音中的“非主流”啊
同样写山,王维就不像李杜那样写。前面我们已说了很多他的山水诗,现在我们只看一首《归嵩山作》,写于开元二十二年,当时王维也赋闲在家,境遇未必比李杜好。但王维怎么写的——“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就像前面说的,车马轻盈,归鸟伴飞,一副无可无不可的超逸与自信。
综上所述,李杜诗以风骨胜,充满冲突美、矛盾美,甚至是斗争美。明人胡应麟早就有过精妙的总结:“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什么意思?就是李杜已非“正音”,而成一种具有突破和开创意义的“别调”。
而王维以和谐胜,是和谐美,是和谐盛唐的主流声音。什么是“盛唐诗”?南宋诗论家严羽认为是“空中音、色中相、水中月、镜中像”,严沧浪正是将王维(或王维孟浩然)当作盛唐正音的楷模啊!
所以我们认为,功多承先的李白,开拓出高远之美的方向;功多启后的杜甫,展现出深远之美的可能;而王维以静与清,代表着平远之美的维度。他们没有高下之分,如果说王维代表“盛唐正音”,那李杜则代表“盛唐强音”。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记者:虽然偶有“三分诗坛李杜王”之说,可是文学史上,王维却一直不能与李杜并列,这是不是历史的真实呢?文学史上,李杜用一章来写,王维最多只能占一节,有些文学史甚至白居易、李商隐都能独立成章了,为什么王维却仍然没有“成章”的待遇?
王志清:文学史误读王维,我前年在北师大讲座就是这个题目。
倘若我们穿越到公元八世纪,你会发现王维地位之高,非李杜所能及。唐代宗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一代贤君,称王维为“天下文宗”,在得王维诗后,“旰朝之后,乙夜将观”;当时的重臣苑咸称王维为 “当代诗匠”;盛唐诗选家殷璠编的《河岳英灵集》,后人公认为唐人选唐诗最佳选本,其选本序里说王维是盛唐诗坛领军人物;“诗圣”杜甫直呼“不见高人王右丞”,说他的诗“最佳秀句寰区满”;中唐姚合的《极玄集》,将入选诗人称为“诗家射雕手”,他将王维列为卷首,是为“射雕手中的射雕手”。请注意,此时已是王维逝后三四十年了,似乎依旧王维独尊。
海外汉学家宇文所安就说:“王维是其时代最著名的一位,也是最早获得声誉的一位”。王维出名是在大唐盛世,是盛唐上升期;李白在长安出名,比王维要晚约二十年,且在盛世下降期;杜甫出名则更晚,他在盛唐时充其量只属二流,是“安史之乱”成全了他,让他进入创作高峰期。如此可见,在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王维非李杜可颉颃矣!
然而中唐以后诗坛重新洗牌,王维的至尊地位被动摇,李杜被抬高至他们从未有过的杰出地位。这是为什么呢?从时代上找原因,就是因为安史之乱后盛世不再,盛世趣味也不再。
我国之有文学史,不过百多年之久。而从“五四”开始滥觞的以政治批判为主之“现实主义语境”,要求文学“参与现实”“介入人生”“干预生活”。在这种“唯现实主义独尊”的文化语境内,王维那种“不露声色、天机清妙”的诗风极难读懂,也极容易被误读,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便不足为奇,事实上他就被定性为“反现实主义诗人”。
时至21世纪,特别是在综合国力、思想观念、美学趣味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代,为什么王维还是这样的命运呢?
记者:您能否举一二例说明文学史是怎样误读王维的?
王志清:譬如对王维一生思想分期的界定,文学史上说,以四十岁左右为界限,即张九龄罢相李林甫执政为界限,他的思想前期积极,后期消极。这种说法与实情极不相符,至少太过粗放。
王维21岁谪被济州,直至35岁知遇张九龄,其间十四五年也近乎销声匿迹,显然不可说“积极”。
张九龄罢相后,王维也没有消极,别的不说,就说他后期的三次“出使”,应该说是很积极的了。第一次出使是在开元二十五年,以监察御史赴西北劳军;第二次出使是在开元二十八年,以选补副使赴桂州知南选;第三次出使是在天宝六年,从门下省转兵部,出使榆林新秦二郡。不到十年,三次出使,两次兵事,一次铨选,从西北到岭南,去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完成重要使命,既要有独立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又要有临机应变解决特殊问题的能力。
能力且不谈,积极是肯定的。何况开元天宝年间对使者的遴选条件,严格到近乎苛刻,那时就有“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的说法。史书上记载:“常择容止可观、文学优瞻之士为之,或以能秉公执法,折冲樽俎,不辱君命者充任,故必尽一时之选,不轻易授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使者须“尽一时之选”,除了政治条件、业务能力,还要有文学水平,甚至还要高颜值,长得帅!所以使者必是君主信任或朝廷倚重者,“不轻易授人”,不是随便哪个阿猫阿狗就能出使的!可见,王维没有真的消极,也根本不是如文学史所说是“被李林甫支出”。
王维在张九龄罢相不久就奉命出使劳军,途中写成的那首《使至塞上》,写得气势超迈,写得雄浑壮丽,写得兴高采烈,没有一点点悲观失落的气息,更不是不是灰头土脸的难堪。一般人都把兴奋点集中在颈联二句,提起《使至塞上》即大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连《红楼梦》里也借香菱之口来盛赞。
王维的诗是以“造境”取胜。霍松林先生说《使至塞上》“构思之奇,谋篇之巧,匪夷所思”。此诗之最妙者在构思也。因此,读王维的诗,要有全篇观念,要有整体意识,而不能只是陶醉于其景物的生动摹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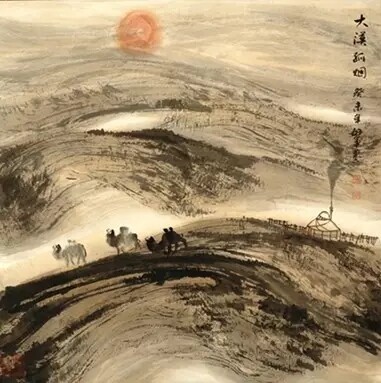
记者:说起王维生平,他在安史之乱中“出任伪职”这段黑历史怕是怎么也抹不去的吧?
王志清:王维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陷贼不死”。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王维真没有问题,也真不是问题。当时杜甫就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老杜《赠王中允(维)》诗云:“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杜甫是非常欣赏王维陷贼后之表现的。
新旧《唐书》里,均载王维陷贼后,不仅不接受伪署,而且以自残来对抗。故而贼平后,王维被肃宗特宥,所有的陷贼者皆受处罚而他却泰然无事,是因为朝廷觉得他无可挑剔,无可厚非。闻一多考察李杜王三者在“安史之乱”中的表现,说王维是“反抗无力而被迫受辱的弱女子”,说李白倒有汉奸的嫌疑,杜甫则是跑丢了爹娘的苦孩子。即便是在王维逝去后五六年,杜甫还是以“高人”称呼王维。
然而,现在仍然有人在“陷贼”问题上诋毁王维人格,似乎对他的道德标准也特别苛刻,这与文学史的“洗脑”有关。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记者:回到刚开始的话题,您为何提出“盛世读王维”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似乎广为认同,上网只要打出“盛世读王维”五个字,“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中国社科网”都在转,连“政协网”“党建网”也转。如何理解这五个字?
王志清:我提出“盛世读王维”,是一种学术预感。王维诗是盛世的产物,他的价值观和思想是盛世的,只有盛世才能读懂王维。
这很好理解,当你身处战乱流离之所,或是阶级斗争疾风暴雨时代,你不能够读王维,也不让你读王维。政治越是稳定,社会越是昌明,经济越是繁荣,人们就越需要高品质的文艺鉴赏。盛世社会,物质高度丰富了,人们也有闲了,王维的读者也就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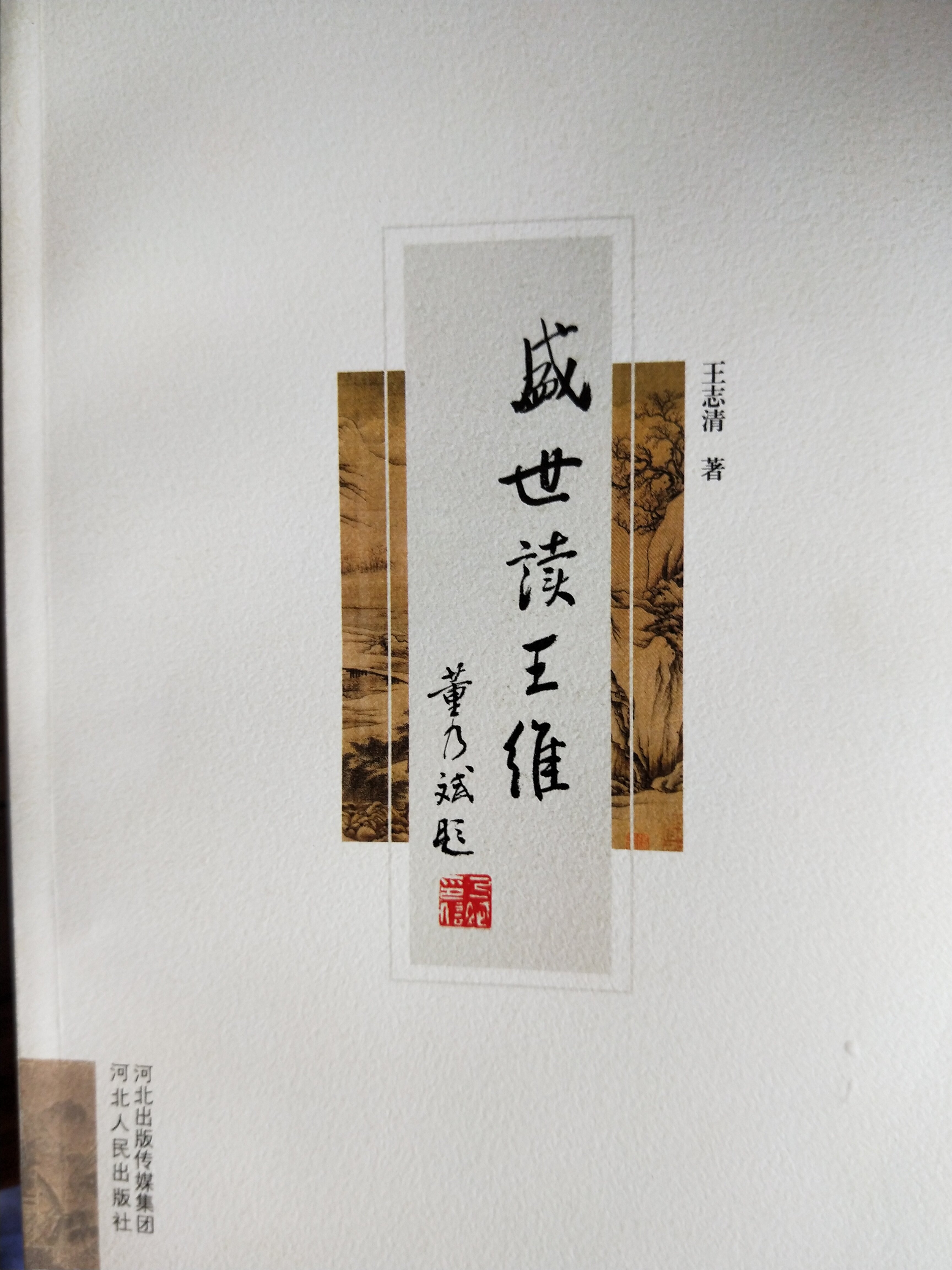
王世清所著《盛世读王维》封面
盛世读王维,我主要从这么几个需要来认识的:
第一,王维的诗使人宁静。中国文化自古“尚静”,王维诗的特质,或者说王维对中国诗的贡献,主要是静上,古人说王维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色籁俱清,读之肺腑若洗”。这是很高的评价,美学家朱光潜就说艺术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诗表现虚静,也能够让人息心静气。当下社会的人,最多的是浮躁,最缺的是静气。读王维使人宁静,这不仅关乎健康,更关乎你对事物对世界的看法。静而不乱,静而自守,自主自由之精神生焉。
第二、王维的诗使人平和。中国文化的典型特质是“温良”,《周子通书•乐上》说“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王维诗最突出特点是对纯美与和谐的追求,内敛含蓄,空灵隽永,从而直抵人性深处。顾随先生说“诗教温柔敦厚,便是叫人平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读王维诗应是盛世读者的首选。
第三,王维的诗使人灵慧。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诚如西方哲人荷尔德林所说“工业文明将人日渐异化”。因此,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都竭力倡导“诗意地栖居”,旨在通过人生的诗意化,来抵消科学技术带来的人性泯灭。王维诗具有一种真正非压抑性的人性自在,读王维,能让我们在物欲横流的环境里气定神宁,尊时守位而知常明变。

记者:当下国学复兴,不久前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等剧集让大家重拾对大唐的兴趣。据我们了解,南通也已成立“王维诗友会”。但王维诗非常精致,也非常精深,怎么才能做一个英国批评家瑞恰慈所说“够资格的读者”呢?换句话说,我们该如何读王维?怎么才能真正读懂王维?
王志清:回归文本!李杜有他们的作品在,王维也有他的作品在,高下优劣皆由他们各自的作品说了算。
我们强调“回归文本”的细读,就是要从被历代解读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文本中,剔出其本来面目。
我很欣赏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的读法,他读王维,将其诗之文本,与其所处历史、文化、社会之大文本结合起来解读,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寻求文学背后的深层含义。他有意忽略了任何现成的研究与观点,甚至没有引用历史上任何一位评论家的现成评价,所以他在王维诗中发现了很多我们在中国文学史里看不到的王维。
记者:读王维对当下有何现实意义?
王志清:我们一直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切自信的源头,也为我们认同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平台。以王维和李杜为代表的唐诗,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中的经典,也是涵养新时代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春节团拜会上向全国各族人民、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时,用“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来开篇,这是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一句。盛世兴诗,盛世读王维。我也想借“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这句话,来形容当下王维研究的态势,眼下虽是秋天,但读王维的春天已经到来,读王维最好的时代已经到来!